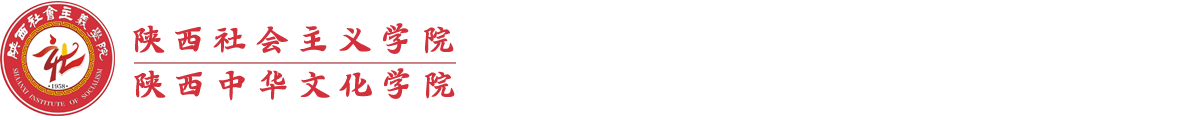
文化 | 书法是雅俗共赏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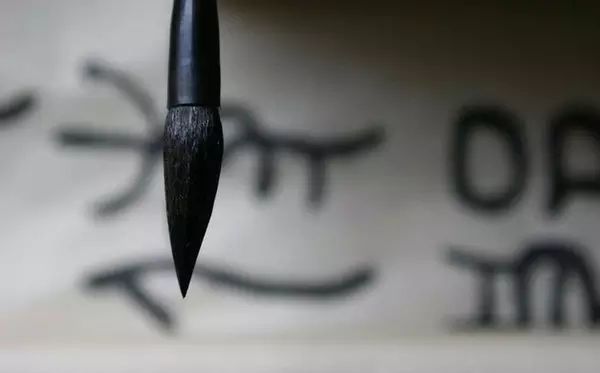
书法是雅俗共赏的艺术
多年来,参加书画活动经常听到雅俗共赏的说法,偶尔也听到雅俗不能共赏的谈论。因此,我不时地思考这个问题。某报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雅俗岂能共赏》。这篇文章的观点很鲜明:书法不能雅俗共赏。围绕这个观点,文章中具体这样论述:“在书法界,常有人说某人的书法作品能雅俗共赏。雅俗能共赏,真是好状态。只可惜,这种状态只是愿望,只是理想”;“什么是雅?雅是阳春白雪。什么是俗?俗是下里巴人。这里雅俗水火冰炭之不同。俗就俗,雅就雅,不能说某一事物、某种书法作品它既雅又俗。这不等于说一个人既是女人又是男人吗?”“仅就某一件事物进行审美,俗就是俗,雅就是雅,没有调和的可能。”
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和论述我认为值得商榷。
首先是这篇文章所运用的论据欠当。因为这篇文章的论据与雅俗不是同一类群。如水与火、冰与炭都是客观实在物,在质上是绝对对立的;男与女也是客观实在物的范畴,虽在人的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在性别上却是绝对对立的;而雅与俗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在质上是相对对立的。相对对立的东西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即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其次是雅俗不能共赏的观点不敢苟同。我以为雅俗能共赏,雅俗是可以调和的,书法就是雅俗共赏的艺术。下面重点谈论这个问题。
从艺术起源角度说,原始、初始的艺术都是普通老百姓的艺术,都是民间民俗艺术。例如,汉代《淮南子·道应训》里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就是古代人民在劳动之中所创造的艺术。再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投足”是一种舞姿,即三个人手里拿着牛尾巴,投足而歌。这表明,我们的祖先刚刚学会说话时,就开始进行歌舞融合的活动。这也就是古代人民劳动之余所创造的艺术。这些艺术是最原始的、最初始的,也是最纯朴的。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观看,它是雅还是俗?的确,无所谓雅也无所谓俗。但若用现代审美标准衡量,当时的艺术都是通俗艺术。
从艺术发展角度说,通俗艺术是高雅艺术的基础,高雅艺术是通俗艺术的提炼升华。具体说,随着时间推移,古代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所创造的艺术也在演变发展,原始、初始的艺术活动必然由单调到丰富、由机械重复到螺旋式重复,这个过程就是古代人民对艺术提炼升华的过程,高雅艺术也因此而产生。因为俗是相对的,俗中蕴有雅的因素。以现代审美观念,通俗艺术是原始的、民间民俗的,是高雅艺术的基础和根;高雅艺术是通俗艺术的提炼升华。因此,雅是相对的,雅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俗的因素。显然,没有俗也就无所谓雅,雅和俗都不是绝对的,因此不能绝对说雅就是雅、俗就是俗。比如《诗经》是儒家经书之一,古代文人雅士必读之,现代大学文科也必学之;但是,它基本是当时周王朝在诸侯国的协助下,采集民间歌谣经过整理而成的,所以是典型的由俗提炼升华为雅的。凡是读过《诗经》的都会清楚地感觉到它的根还深植在俗中。如《诗经》第一首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首诗无疑是雅的,但是不能说它没有俗的因素。它是由俗升华为雅的,是雅俗有机融合的典范。孔子对这首诗的评价是八个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再比如,京剧是国粹,绝对是雅的。但是,它形成于200年前几种古老的地方戏,特别是十八世纪流行于中国南方的地方戏徽剧(安徽地方戏曲之一,流行于该省和江苏、浙江、江西等地)。1790年,第一个徽班进京,参加乾隆皇帝80岁生日演出。随后又有徽班陆续到北京演出,加上北京聚集了很多地方戏种,徽班又善于吸收其他戏剧艺术的特色,故徽剧在艺术上迅速提高,逐步演变发展成为中国最大、享誉世界的戏曲剧种——京剧。可以说,京剧是以南方流行的地方戏剧徽剧为主,融合流行于西北地区的汉剧和南方的昆曲及河北梆子等众多地方戏剧演变形成的。地方戏剧又是由民间戏剧演变形成的。因此,京剧是典型的由俗演变升华为雅的。俗是根,雅是叶。京剧由于俗的根深,所以雅的叶茂。
另外,从艺术关系角度说,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由俗升华的,它的根在俗中,俗是雅的基础,所以雅与俗是可以调和、转换的。如“人民哲学家”艾思奇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了24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以《哲学讲话》结集出版,并在第四版时更名为《大众哲学》。自问世那天起,该书一版再版,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再如1938年,朱自清先生受人之托写了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书,后来“意无不达”、“雅俗共赏”的《经典常谈》便问世了。至今,该书多次印刷,本身成为人民大众的经典。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与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雄辩证明,高雅文化艺术与通俗文化艺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调和、转换,而且可以让高雅文化艺术转变为通俗文化艺术。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艺术的雅俗不是固定不变的,关键在于创造合适的条件,促使二者之间的调和、转换。就书法而言,它从造字而成为艺术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好地说明了书法所兼具的雅俗艺术的特点。
从书法与汉字关系来说,汉字先于书法产生,汉字是书法的基础、载体和表现对象,书法是汉字的衍生艺术。因此可以说,在汉字发明并进入较为普及的阶段后,上层人士书写汉字衍生书法艺术;但是不能说,普通百姓书写汉字不能衍生书法艺术。书写汉字衍生书法艺术不是上层人士的专利。因为一种汉字体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它是在普及书写的过程中逐渐自然形成的。字体如此,书法也必然如此。比如隶书就是战国时期在民间流行的书体,经过秦到东汉逐渐改变和美化的。从隶书形成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上层人士书写汉字衍生书法艺术,普通人士书写汉字也衍生书法艺术。
从书法实践说,中华民族这一传统的艺术能延续数千年而不衰,甚至在电脑代替手写的今天,似乎有空前蓬勃之势,这与上流社会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同书法艺术结下不解之缘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古至今,宫廷、官衙、家庭都以陈设书法作品而显雅致;殿堂、寺院、亭台楼阁悬挂楹联尤显风雅;即使不通文墨之人也要挂书法作品以避其俗;至于春节,中华民族不分阶层都要书写悬挂春联,春联更是丰富多彩。由此而言,书法艺术自古以来各阶层都在创作、都在欣赏、都在有意无意地促其发展。
再赘述几句,雅俗融合的艺术,即雅俗共赏的艺术才富有生命力,才更有价值,才能流传下来。比如《诗经》共收诗歌305首,分“风”、“雅”、“颂”三部分。在当时“颂”诗40首被认为是绝对雅的,而“风”诗160首、“雅”诗105首是相对雅的。但随着时间推移,“风”、“雅”诗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尤其“风”诗,历代文人雅士普遍以“风雅”作为创作方向或标准,不少“风”、“雅”诗篇诗句至今还脍炙人口。比如《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又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再如《卫风·氓》“……三岁为妇,靡有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等等。由于“颂”诗属于宫廷文学,所以只是对封建社会善于歌颂“圣明”的文人有一些影响,谈不上流传。
综上所述,书法确能雅俗共赏,而且本身就是雅俗共赏的艺术,也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岳崇
全国政协委员
民进陕西省委副主委
文史学者、书法家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5年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