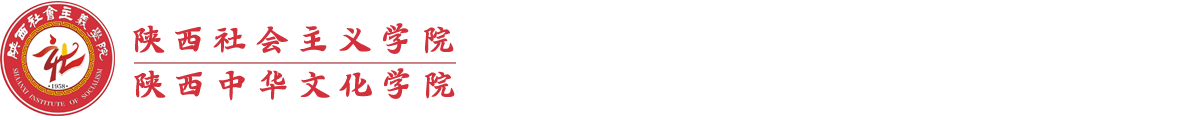
梦里依稀乡土情
(陕西省第二期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 王黎萍)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当文人们仔细搜索城市的每个角落,想在力透纸背中表达一种对人性的终极思考时,却发觉千城一面,繁华的城市丢掉了文化之钙而没了生命之根,变得苍白一片;熙熙攘攘热闹场面没有历史的积淀变得轻飘飘的,像丢了魂的人似的,城市浮躁的表象脆弱地承载不了深沉的思考,不得不在钢筋水泥之外寻找精神的脊梁。或许儿时的一切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盛满了对父母劳作场面的温馨回忆,装满了儿时伙伴们调皮捣蛋的欢笑,抑或当时的某种嬉闹或者恶作剧,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种奢望和幸福;或许这儿时记忆就是今生的精神底色,无论经过多久都不会褪色;或者他还不能在方寸之间,用朴素的文字表达悲天悯地的情怀;不能于空灵剔透中,从纷繁中把握简单的质感;或者他的阅历还不够,还不能从城市大而宏阔的变革中辨明应有的价值取向,不能自如地驾驭素材;或者他被卷入信息泛滥漩涡,不能用宁静的心过滤沉淀社会的浮尘,形成或宁静美丽,或深邃悠远的文字;或许他的身体挤进了城市,思想习惯还没有融入城市,城市的主流思想、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圈子都没有接纳他,当别人沉迷于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时,他只能在冷清的斗室,倾情于乡土文字,熟悉的乡土成了这些人内心涓涓细流的归宿,乡土文学成了浅吟低唱的一种乡土情节,他们不一定深深热爱乡土,乡土却能承载他们的情怀,慰藉他们的灵魂。
做工精美的旗袍配上或高雅或雍容的造型,穿在或浓妆淡抹,或婀娜多姿,或端庄贤惠,或秀美空灵的女子身上,在举手投足间一切都显现了出来,这是一种衣着文化。独特的少数民族的服装,尤其是嫁妆,还有那原生态的歌声,蕴含了多少民族的血脉?这些在今天的城市日常生活中还能找到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般安享清幽的闲适我们有吗?喧闹中独自轻啜红酒能享受内心的那种静谧吗?文人们不由得把笔墨给了熟悉而又承载着历史文化的风土人情。
每一种习俗都会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独特的风俗也是了解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金钥匙。自梳女可谓是一种悲壮的女权运动,虽然女人已经积极参与手工作坊,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但是封建礼教还在盛行,自由恋爱的风气未开,有些人对包办婚姻不满,有些人对旧婚姻感到恐惧,有些人为了帮父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而毅然决然地邀亲请友,敬拜天地,梳起发髻,终身不嫁,走上了一生独居的道路。这或许多少受到了宗教文化的影响,寻求自由的她们却并没有与世隔离。这自梳女就是作者笔下一道亮丽的风景,即消解了成长过程中能力和储存不足的恐慌,也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
泉州的惠安女是精美石雕的代名词,服饰独特,婚后久在娘家居住。如果熟悉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就会联想到惠州的男人们随着发达的航运常年漂泊在外,甚至纷纷下南洋打工经商,女人们则承担起了家里的一切重活累活,石雕也成了她们的看家本领。这样在历史背景下,从地域经济发展中就解读出惠安女现象源于当时的社会和家庭分工。作者或许就演绎出一名结了婚的惠安女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望南洋中,盼不到丈夫归来的身影,孤苦无奈中就常年居住在娘家,把对丈夫的深切思念化作了石雕上丈夫清晰的影像,久而久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影雕。让人们想到惠安女头上的帕子当然是遮挡雕刻时产生的粉尘,以雕刻为生的女人大概整日也离不开围裙,那么漏肚脐眼就不是时尚,而是长衣服穿在围裙下太热。感受到是久别离的生活造就了惠安女婚后长期在婆家生活的习俗,而不是奇特的惠安女创造了这样一种异样的风俗。
或者从一个小小的女人使用头发夹子生发出一番忠孝礼仪的感慨来。解读陕西合阳一代女人使用头发夹子的习惯,他就会援引《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理解这是中华深厚孝道文化在生活中的体现,女儿远嫁,不能侍奉报答父母,就小心翼翼地把来自于父母的发肤妥善地保存起来,这或许是女儿远嫁后,见不着父母,保存落发表达对父母的忠孝之心,寄托思乡之情。发肤之情感牵连演化,表现形式很多,如男女以青丝相送表示爱慕思念之情;新婚夫妻各剪下一撮头发接在一起,称为结发夫妻,表示不离不弃,白头偕老;发小则是一种手足之情。
乡土中也有许多熟悉的情景,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鸣,而愉悦读者。看着三寸金莲,中年人就会想起奶奶那辈人的小脚和悲惨生活,三寸金莲就是那个时代女人社会地位的写照,站不稳脚跟,没有广阔的天地。想起家乡一对蓝色枕,留下两行辛酸泪。耳枕的主人在青灯陪伴中,渴望圆房的那一天与丈夫同枕而眠,苦苦等待了11年,却得知从未谋面的丈夫阵亡了,才开始用心爱的耳枕。蓝色的温馨,青涩的愁绪,如今谁还能为未曾谋面的人而独守空房11载呢?随文轻声探问,感情到底是男欢女爱还是一种忠贞不渝的文化呢?追问那些花容月貌的女子们读到耳枕女人的故事,能否守住自己的节操?拷问那些渴望红颜知己的人们是否仰慕耳枕女人的坚贞?一对不起眼的耳枕竟成了一种精神和思想的风骨。
纺锤、棒槌、绣花的花绷子,一下子也会把中年人拉回到对母亲的无限思念中。不觉想起儿时每当梦中醒来,母亲还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摇着纺车。天气好的时候,母亲会提上一笼子衣服到水库去洗,母亲用棒槌捶打着衣服和皂角,使劲搓洗着衣服。如果是粗布被里,快晾干时,再用棒槌在青色的棰布石上锤平展。夏天的午后,或在一株浓荫密闭的大树下,或在一间宽敞明亮的门房过道里,相好的女人们聚集在一起边做针线活,边拉着闲话。有的用纺锤纺麻绳子,纺锤转的欢快极了,就跟女人内心的幸福和脸上灿烂的笑容一样;有的在纳鞋底,把绳子绷得紧紧的,针脚也抻得平平的,好让家人穿着既结实又舒服;一位大姑娘正专心致志地绣嫁妆,对于配线或者针法吃不准,羞怯地问嫂子,婶子们借着机会开大姑娘的玩笑,这时候那闭月羞花的容貌便绯红一片,化作了嫁妆上那鸳鸯戏水缠绵情,鱼戏莲下爱意浓。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生动活泼的场景和邻里情深,男耕女织的乡村生活连同那个时代淳朴的欢笑,充满热闹的场面已经一起走进了博物馆。只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独自坐在年久失修的家门口,守望着池塘边荒芜的田野,没有爹妈照顾的孩子如同放牧般留在荒芜的村庄里,甚至姊妹五个人落水了,也找不到一个年轻人去救救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我忍不住叹问,亡故孩子的父母有错吗?他们难道不想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明天吗?难道城市的繁荣必须以农村的荒芜,留守儿童精神的荒废乃至身心惨遭伤害为代价吗?打工者的悲欢离合以及与打工者密切相关的乡村的命运,也被草根们用丹心书写着,棒棒军在城市里的生活是用肩扛背挑一步步丈量出来,是一滴滴的血汗换来的。城市牢固的房屋是建筑工人吃咸菜啃馒头睡湿地板的煎熬中建起来的,明亮的内墙是油漆工在闷热中顾不上戴口罩,损害了自己的身心装扮出来的。当官员们包养情人过着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时,打工的汉子们却长年忍受着夫妻分离的性饥渴;当城市的人们小病大养的时候,生病的打工者们却畏于昂贵的药费,在凛冽的西北风中硬扛着。他们难道不想体面的活着,健康的活着,幸福的活着吗?他们能吗?
是这些保持有一定文化底色的风土人情能给人一种启示,是乡村的淳朴能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是乡土的多面性,既能安放人们高贵的灵魂,也能用朴素文字承载真挚的感情而打动人心;是亿万个还没有麻木的人们需要陪陪星星和月亮走一程,任凭对家乡或眷恋或思考随着键盘的敲打而流淌,换来明日的扬眉吐气,或许这就是乡土文学俯首皆拾的原因吧!
(教务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