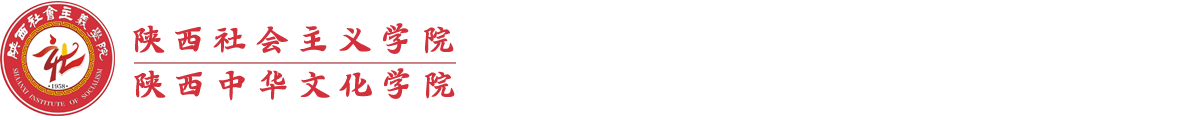
两 条 床 单
(陕西省第二期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王黎萍)
画家禅雪师父特别喜欢土织布,让我帮他找两条,这年月到哪里寻?记得陪嫁的床单还有两条,翻箱倒柜只找到了一条,母亲在家小住时已经用开了,好在床上铺的还有两条婆婆织的,画家也不嫌弃旧。两条床单要离我而去了,不禁思绪万千。
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家中不大的房子总放着一台老式织布机,纺车也不离炕头。打自从有了自留地起,母亲就喜欢在离家远的旱地种棉花,棉花不好发芽,要用地膜。生棉蛉了,没有帮手的母亲默默在家兑好了1605农药,呼哧呼哧地背上几里地去打药。有时候药味太浓会把母亲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能赶上给我们做饭,妈妈总是强忍着继续打。每打一次药母亲都要难受几天,肩膀也磨得红红的。棉花容易疯长,想多结些棉蕾,提高产量,母亲就起早贪黑地做饭、喂猪,早早趁凉快拿着馍提着开水,走到五六里远的南岭去打尖、梳花。骄艳的烈日催熟了棉花,妈妈开始忙着摘棉花,这是个数儿活。只见妈妈把围裙在腰里围折成兜,两手指头飞快地插进吐着棉絮的花蕾,捏紧了一拽棉花就从壳里揪出来了。没开大的棉花是摘不出来的,开大了没捏紧的棉花拾不干净。头顶烈日,母亲顾不上擦擦额头和脸上的汗水,心里却盼着太阳更毒些,让棉花开大些,棉花更筋道,也多产些棉花。
拾了棉花,母亲就到场里去晒棉花,边晒边把夹杂在棉花中的棉叶子拣出来,要不然将来的棉花里杂质多,棉花不白。到了秋季,太阳不好,淋雨也多,该腾地了,就把没开的棉花骨朵连同棉花杆拔回家,趁着好天气,再晒出来些棉花。棉花全晒干了,母亲会把棉花根据好坏分出来,去拧棉花,也就是把棉籽脱出来,脱出的棉籽用来换油吃。然后再弹棉花。弹好的棉花,或者用来做被褥棉衣棉裤或者用来织布。如果要织布,就得先搓捻子,再把搓好的捻子纺成线。纺好线有的做穗子,有的拐好了经布。为了增强布的韧度,还要把线浆一遍。如果要织花布,还得先到染坊染线。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总是点灯熬油织布纺线。冬天的晚上母亲安顿好我们几个,就坐在炕头纺线。母亲拿捻子的左手总伸得远远的,好让线纺得细而匀称;纺车摇得稳稳的,把锭子纺得平平整整。母亲纺线的声音特别好听,像小鸟叫唤一样,支咛咛咛咛,也像催眠曲,我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稀里糊涂听到公鸡喔喔叫的时候,隐约觉得妈妈才和衣小睡一会,白天还要忙着地里的活计。
然后再作穗子、投筒。穗子是织布的纬线,筒子是用来经布的。经布要天气晴好,请上几个能手,拿了织布的绳,顺着路把橛钉好,把桐子上的线一根根穿过绳的缝隙,拉远了,再卷在线架子上。想织格子花布,就按照花色品种把筒子线按花色排好。为了线不交织在一起,经布不但要用刷子把线梳顺,还要加上小梢棍卷紧,织的时候才不会松垮和断头。经好的布架在织机上,妈妈腰里攀上厚牢结实的带,脚蹬着沉重的脚踏,一手飞舞着梭子,一手使劲搬动着织绳。花布的纬线要频繁换不同颜色线的穗子,随着笨重的哐啷哐啷声,布就慢慢地织出来了。
母亲是位特别爱好的人,在织布中用绳向怀里把新织的布给紧打的时候,就把腰使劲给后背,好把布拉紧,当然也要不断地换压布的铁绷子,这样母亲织的布又平又紧又密,大家都喜欢看母亲织的布,学母亲布的花色和织的技巧。凭着良好的手艺,在还没有分产到户前,母亲就用给人家织多少丈布或者节省出来的布票来顶替部分短款,好接济生活。由于长期脚上用劲,母亲脚面比原来高了许多,脚踝也变大了,穿一般型号的鞋子总是很夹脚。
就这样,我们姊妹几个每年都能穿上母亲做的新粗布衣服。我把母亲织的白蓝相间的床单紧紧抱在胸前,母亲劳作的身影一幕幕在眼前流淌。脸贴在床单上,仿佛还能感受到母亲身体的余温。母亲陪嫁我床单,不只体现着母亲的贤惠、良好的耕织和料理家务的能力,给我体面和荣耀。也把她勤劳勇敢和朴素的爱美情结深深烙在我心灵深处,不服输的倔强性格大概就像母亲这平展厚硬的布,母亲的品质大概就这样随着织布声织进我岁月的年轮,成为生命的底色,无法消退,难以忘怀。抱着母亲织的床单,我久久地深思着,舍不得给别人,觉得只有母亲才配得上铺这样的床单。
婆婆的床单红白蓝三色相间,花格子比较大,线比较粗,布边参差不齐,织得也比较松软,没有母亲织的床单那么平展好看美观,但是手感很好,睡着也很舒服,而母亲织的床单虽然很平展,但是很硬,刚开始用的时候不舒服,而且色泽灰暗,格子太小,铺在床上没有轻松的感觉。看着这两条床单,我不禁再想,母亲床单中融入的过分固执和倔强,也是这样的令别人不舒服,但是母亲却认为很完美,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着,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每一个细节。母亲也常常夸赞婆婆干活很巧,比她出活。我曾顺势跟母亲说,没必要把什么事情都作得非常完美,而让自己很辛苦。母亲说,她已经成了这样的一种心性,很难再改过来。看着婆婆的床单,这是一种柔性的生活方式,她也在努力,但是有一个度,自己不是很辛苦,别人也能接受。母亲的床单就像一个人把自己隐藏的很深,独立特行的生活,自己的内心很强大,无需经常与外界或者他人交流,别人也很难改变她,但是没有交流就没有朋友,可能也会感到孤独,是内心深度的孤独。婆婆的床单就像一位外向健谈的人,她很能干,也无须掩藏自己的喜怒哀乐,总是一吐为快,她在强势中无须求别人,可能活得很潇洒。
此刻,怀抱的不只是两条床单,更是一种情感和精神的寄托,我舍不得给别人,但是母亲和婆婆愿意成人之美。妈妈们的大度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我想给那两条床单拍照留念,又怕以后触景生情,就下狠心把床单邮寄走了。想写文记录下来,懒散得动不了笔。月初去武功县蓝可村参观手织布,他们的纺纱、落筒和经布都机械化了,对传统织机作了很大的改进。原来的两个缯改为四个滑轮,原来前后两个踏板变成并排的四个踏板,直铁绷子成了蛇形的绷子,无须像以前频繁换了,单线纬线成了双线,也没了腰带。织娘比以前轻松多了,无需熬夜一天可以织5米布。
古老的织机原本在我们不断穿洋布的时候,连同纺车已经被人砍烧柴火了,随着一村一品活动的开展,武功县开发了苏惠手织布,使得家乡已经退出生产的织机得以改良,并发展为致富的产业,当人们一百元从农民手中买了一件粗布短袖,感觉价高时,怎能体味到这其中原本的辛苦呢?我也再次想起了那两条床单,随着键盘敲打着心情。

